作者:涟韵男孩
引子:
大明武宗皇帝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
正是七月流火的季节,暑气渐消,秋意悄无声息,虽凉却淡,街边的细草似也微微黄了些。
太祖立国已有一百五十年,永乐迁都也过去近百年,南京这曾经的京师却繁华如昔。它没有北京的朔风凛凛,也没有成都的云雾缭绕,它有的是大江东来的雄浑和烟雨蒙蒙的恬静,刚与柔,在这座宁静古城的没一个角落中交错着。
街上人来人往,江湖武人与贩夫走卒的喧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一切都显得太平安详。
一队沉默冷峻的黑盔军兵照例巡过长街,人群中的喧哗声忽然不约而同地压抑沉闷了几分。
那是宁王府的亲兵。
武宗皇帝年青,一向喜好游荡玩乐,极为厌恶繁重的政务。朝政被八个亲信太监掌控,人称“八虎”。世居南京的宁王朱宸濠趁机重金买通八虎之首大太监刘瑾,竟然恢复了被太祖成祖两代废弃的宁王府卫兵,时至今日,宁王府已有万余护卫。宁王更暗中收买吞并应天周边各路黑道帮派和盗匪响马,暗中积蓄了庞大的势力,俨然已经在应天府一手遮天了。坊间更有知情者暗传,宁王怕是有不臣之心了。
仲夏的南京城,已是风雨萧萧,云雾重重。
(一)金陵风雨
江南的雨总是细腻温润得像是少女的眼眸,下在清凉的秋夜里,便染上了几缕轻烟似的愁续,风吹过,薄雾淡然。
夜市早早散了,宽阔纵横的街道冷清了下来,只有万花楼还在朦胧的雨幕中灯火通明着。
万花楼,名字很俗气,却是南京城里无人不知的温柔乡销金窟,每个晚上都是它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有数不清的千娇百媚的美妙姑娘,自然也有的是一掷千金的豪绅大贾。进出那两扇雕花牡丹的朱红大门的人,无论是王孙显贵,风流才子还是江湖侠客,都飘飘然一副醉生梦死的模样。
江序此刻就坐在这万花楼最有名的潇湘阁中喝着酒,锦衣玉带,俊逸出尘,神情懒散地看着窗外细细的雨丝,一副膏粱子弟的浪荡姿态,像极了那些日日在此花天酒地的少爷公子,却很少有人能想到,他竟然是公门中人。
江序今年二十六岁,他原本是个狼迹江湖的少年侠客,五年前为报答赣南巡抚王守仁的救命之恩而投入公门,被内阁大学士费宏破格录用,数年之中就升任应天都指挥使司指挥使,统辖应天府及周边州县的各路卫军。这人文武双全,手握重兵,却始终改不掉一身风流气,每月的俸禄除了酒钱差不多都扔在了万花楼里。
万花楼半年前新来了一个琴舞双绝的花魁,名叫幻雪,短短几个月就名动一方,江序好不容易赶上一晚空闲时间,立刻抽空跑了过来。
老鸨子知道这位爷的脾气,奉上一壶好酒刘早早退了下去,留下江序一个人静候芳踪。
“小女子被一点俗事耽误,让江大人久等了。”过了许久,江序眉头忍不住皱起来的时候,一个温润酥软的声音才柔柔传到阁中。其中那抹清澈空灵的味道,让久居江南,听惯了吴侬软语的江序也不禁双目一亮。阁门轻启,一个云鬓玉簪的妙龄少女莲步轻移,摇曳生姿地走进来。
这少女只有二十岁上下,正是最好的芳华,娇躯高挑苗条,玲珑诱人,面若桃花,眉如墨梅,最美的却是那双眼睛,清澈灵动如闲花流水,纯净得没有染上一丝一毫的凡尘,不经意的一个眸光,就像一抹清清凉凉的月光拂过,让人煞时间忘却了心底一切的烦厌,整颗心也随之空明干净起来。
江序实在没想到,这个万花楼艳名远播的花魁姑娘居然有这样一双清澈的眼睛,两人的眼神一触即分,江序心神一荡,随即目露一抹奇色,瞧着她的目光多了几分异样的意味。
少女的原本平坦的小腹居然高高隆起,把宽松的纱裙都撑起了一个美妙的弧度,看样子至少也要有七个月了。这位名动金陵的幻雪姑娘,居然是身怀六甲,挺着一个大肚子!
江序惊讶之余不由得更是心动不已,这姑娘大着肚子都能争到花魁的名头,想必她的瑶琴妙舞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遇上江序火热肆意的目光,幻雪向他含羞一笑,柔柔地低头下头,却是不动声色地把一抹冷光深藏进眼底。
江序手握数万精兵,正是大学士费宏钳制宁王的杀手锏,宁王早欲除之而后快。但江序武功高强,生性谨慎的朱宸濠隐忍数年,这才要对他下手。幻雪正是来自换日阁(宁王网罗邪道高手所创的杀手组织,凶名昭著),为了等这个晚上,她已经在这个她原本极为厌恶的烟花之地逢场作戏了半年。
只因这是宁王要她去做的,只要他想做的,无论什么,她都会替他完成。
幻雪和羞抬头,缓缓走到江序面前,扶着肚子福了一福,轻笑道:“还请大人不要见怪才是。”语音娇柔,浅浅低笑,那份若不禁风的少女姿态分外惹人怜惜。
江序随手倒满一杯酒,懒散地把酒杯夹在手指间,似笑非笑道:“那我若是见怪呢?”幻雪受惊似地幽幽望了他一眼,忽然伸手接过酒杯,咬着樱唇一饮而尽,紧接着再倒满两杯,都是毫不犹豫的酒到杯干。
她喝酒的时候,身上似乎有种男子般的英气,酒喝完,俏脸上却悄悄浮起两抹晕红,眼波也更柔软了一些,她柳腰轻折,再给江序倒上一杯酒,纤手捧着酒杯柔声娇嗔道:“这下大人可满意了?”
“姑娘酒量不错。”江序接过酒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幻雪娇艳粉红的娇颜。这个姑娘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妩媚,却与那些烟花女子放荡诱人的媚惑不同,她的妩媚带着抹掩饰不了的稚嫩清纯,娇怯怯的姿态让她在他眼中越发美的让人窒息。
江序对这个少女充满了兴趣,他意味深长的笑了笑,仰头喝尽杯中酒,笑道:“听说姑娘的琴曲歌舞都是金陵一绝,今天在下应当能大开眼界了。”
见他喝下那杯酒,幻雪眼中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她捋了捋垂在耳畔的一缕青丝,微笑道:“一点上不了台面的玩艺罢了,倒让大人见笑了,不知道您想听什么曲子?”
江序玩味的目光落在她饱满浑圆的肚子上,嘴角浮起一抹坏笑,道:“听曲儿倒不急,不如先看姑娘跳一支舞吧。”
幻雪美目含情地嗔望他一眼,玉手轻轻抚摸托抱着大肚子,轻声道:“妾身现在这个样子,大人不嫌弃么?”江序笑道:“姑娘生的国色天香,无论怎样,都是别有韵味的。”幻雪柔美地一抿樱唇:“那妾身只好为大人跳一支舞了。”
嫣然一笑,幻雪修长雪腻的藕臂已经出水芙蓉一样轻轻抬起,紧接着是香肩、玉背,沉重的大肚子有些笨拙的缓了缓,莲足轻移,她整个人已经犹如一涓清流一样舞动起来。轻风吹过水面,惹起一池微波,幻雪娇柔美妙的娇躯也犹如水波一样细微温柔的颤动着,薄纱轻扬,她美如暖玉的肌肤若隐若现,一抬手,一收足,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少女温婉柔媚的动人意味。
这是一支江南常见的舞蹈,没有名字,在采莲女中流传了很久。幻雪像一个纯洁率真、采莲归来的少女一样自由自在的轻盈起舞。将近八个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有些笨重的大肚子累得她好多动作都似乎都有些笨拙,却又别有一番柔弱娇憨,惹人怜惜的柔美孕味。
曼舞中,她忽然向他甜甜一笑,竟然让他在一瞬间有些失神。就在这时,曼舞之中的幻雪柳腰微摇,玉首轻扬,长可及腰的浓密青丝便给她巧妙地甩得旋转飞舞起来,发梢轻轻碰触到江序的鼻端,冷香幽幽,撩拨得他的心神也是微微一荡。那支束着发髻的玉簪便在这时倏地自秀发中弹出,冷电般疾刺江序咽喉!
这一簪来的太过突然,即使是成名多年的暗器大家,也难以发出如此诡异狠辣的手法,何况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江序脸上却并没有惊慌之色,他双目一冷,脚步一转就要侧身躲开。以他的武功,躲开这簪子无疑是易如反掌的,可他竟然没有躲开。
江序才一挪步,一股针攒般的剧痛就腾地从丹田中汹涌而出,他居然提不起半分内力!他身子只来得及偏了偏,那支玉簪已经深深刺入了他的肩头。江序目光一震,眼中终于露出几分惊色,沉沉望向正默默望着他,似乎从未动过的幻雪。
幻雪妩媚娇柔的俏脸已经变得冷若冰霜,但美眸之中却有一丝讶色,淡淡道:“中了‘钟情’以后还能避开这一簪,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江序不动声色的暗中连催内劲,却始终毫无用处,他越是运功,丹田中的刺痛就越是厉害,转眼工夫额头就见了汗珠。
幻雪抬手拢了拢披散的头发,冷冷一笑:“别白费力气了,‘钟情’已经锁住了你的内力,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毒发身亡。”
“原来这毒叫‘钟情’,江序居然笑了笑,生死关头,他却像是毫不在乎,居然又坐回了椅子上,问道,“姑娘想必是来自换日阁了,不知是乱雪还是玲珑?”
“乱雪,”真名叫作乱雪的女子冷眼望着他,淡淡道,“你选错了路,早该知道有今天的。”
江序点点头,眼中忽然露出一抹不同于他一贯懒散的坚毅之色,坦然道:“士为知己者死,古人尚且如此,何况今人?”说着,一仰头,提起酒壶把剩下的多半壶酒一口气灌入喉中,用袖子随意抹了抹嘴角的酒迹,这才笑了笑:“能否让我死个明白,这毒是怎么下的?”
见他神色平静,没有丝毫恐惧之色,乱雪却也并没有急着下手,冷然道:“你一直在怀疑我,我得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可你忽略了一件事,下毒并不一定都要用手的。她瞥了眼那个翻倒在桌子上得酒杯,素手轻轻抚摸着隆起得肚子,“我喝那杯酒时,并没有做任何事,毒是涂在嘴唇上的。”
“原来如此,”江序恍然道,终于面露一抹苦笑,“姑娘好厉害的手段。”
乱雪冷漠地望着他,并没有接话。沉了一沉,才开口道:“你总算还有些气魄,我会给你个痛快。”纤手从被肚子撑得鼓鼓的纱裙腰带后拔出一把长约五寸的短剑,挺着大肚子缓缓向他走过去。江序似乎认命一样闭上眼睛,面无表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乱雪一步步走过去,脚步不急不缓,见江序始终再没有反应,眼中的冷意却越来越浓。她终于走到了江序身前,没有犹豫,手中短剑一抖,斜斜刺向江序的咽喉。她地剑法并没有暗器那样快而诡异,剑意舒缓飘渺,如同风吹碎雪,但一点寒芒已经遥遥封住了江序胸口以上的数处大穴。
江序忽然睁开了眼睛,怒目一瞠,张口一吐,一股酒浪猛地从他口中吐出,直扑乱雪面门。江序武功奇高,虽然已经身中奇毒,乱雪仍是对他存着几分忌惮,他猝然发难,她虽惊不乱,短剑轻飘飘地回手一挡,已经稳稳护在身前。
乱雪应变虽及时,可江序吐的是酒,酒浪撞上剑刃,登时被激得四散飞溅。乱雪只觉脸颊一凉,江序人已经虎跃而出,翻手拍出一掌。他武功走的是纯刚猛的路子,一掌才出,凌厉的掌风已经迫得乱雪衣裙飞乱,竟似是没有中毒一样。江序这一掌来的好快,乱雪平常之时尚且难以避开,何况这时挺着沉重笨拙的大肚子?她美目一寒,他的铁掌已经拍到了她身前!
乱雪已经来不及招架躲闪,她一咬樱唇,捧着大肚子不顾一切地身子下蹲,为了护着肚子竟是要用胸口挨这一掌。江序先前是坐着的,这一招“长河落日”平平拍出,眼看就要击中乱雪鼓隆浑圆的肚子,他终究是心中不忍,奋力振腕将这一掌向上偏了几分,乱雪身子一低,正是无声无息地拍中了她胸口。乱雪娇躯一震,身不由己得斜滑出几步才踉跄着站住,俏脸上已是苍白如雪。
江序这一掌掌力虽雄厚,但后力却明显难以为继,可乱雪一身内力七成都不管不顾地护着肚子,被他阳刚灼热得掌力透胸而入,实在已经受了不轻的内伤。她只觉胸中如遭火焚,一口鲜血差点儿就要急涌出来,却被她咬牙咽下,捂着胸口娇躯漱漱颤抖,一双美眸惊疑交加得盯着江序。
一击得手,江序却没有再出手,他甚至都没有再看乱雪一眼。
刚刚江序吐出酒浪,是一门“醉解千愁”的驱毒妙法,可以借着灌入腹中的酒来回冲荡,最终化解毒力。可他喝下的酒太少,时间又太短,仅仅够他勉强压制毒素,但这名为“钟情”的奇毒太过霸道,早已渗入了他真气之中,他发出那一掌时已经存了玉石俱焚之心,虽然打伤乱雪,自己也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一股暗青色在江序脸上渐渐浮现出来,嘴角也淌下一抹黑血,他仿佛被抽尽了所有的力气,却还是艰难得向后靠住墙壁,缓缓向西方望了一眼,轻轻笑了笑:“大人,江某没有完成答应你的事,无颜见你了…”他高昂的头缓缓垂下,声音渐渐变低,似乎有声叹息,却终于寂静无声了。
乱雪慢慢低下头,轻轻抚摸着温热柔软的大肚子,默然无语。刚刚他可以杀了她的,以那一掌的凌厉,如果打她的肚子,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是不可能受的了的。这个孩子是他的孩子,如果孩子没了,就算她能活下来,她都不知道自己肯不肯再活下去…
乱雪抬起头,怔怔望着那个高瘦的身影,他没有束手待毙,也始终没有倒下,哪怕他已经死了。她习惯了冷漠的眼中忽然露出一抹凄然,喃喃道:“对不起…你对我手下留情,我却杀了你。可我为了他,做什么都不会后悔的,不会…”她转头往向窗外,眼角却分明含着一抹泪光,像窗外的雨那样冰凉的泪光。
阁中的动静终于惊动了老鸨,她带着两个匆匆赶来的伙计颤抖着声音在扣门。乱雪知道这附近就有南京守备司的兵营,她怀着七个多月的身孕,又受了伤,一旦惊动了江序通辖的卫军只怕就难以脱身了。还剑回鞘,她的神色自己恢复了冷淡,扶着肚子走到窗前,玉足在一个木凳上一撑,娇躯已经借力跳出阁窗,轻飘飘落在长街中央。虽然撑着大肚子的腰身有些笨重,身法仍是轻盈灵动。可她才一落地,江序侵入她体内的那股灼热掌力便是一阵翻腾,乱雪压抑不住得吐出一口血,颤抖着身子痛得俏脸惨白,她知道自己这一回竟是受伤极重,惊骇中多少有些侥幸,江序武功之高,似乎超出了她的预测,若非他中了“钟情”之毒,以她现在的孕体,只怕连一成的机会都没有。
身后已经听到万花楼里乱作一团,显然已经发现了江序的尸身,老鸨的惊呼都透着惶急。
乱雪不敢久留,更别说静心运功疗伤了。深吸一口气,乱雪勉力运功压制伤势,扶着大肚子施展轻功沿着一道小巷逃离。她大半真气都用来护着孩子,留给自己并不多,好在她的内力是阴柔一路,跟江序阳刚的内力相互克制,这才勉强能抵挡他的掌力。可她稍一用力,这道掌力就在体内随着经脉横冲直撞,奔出不远,她已经没办法再运转真气,只好咬牙挺着肚子虚晃着脚步往前奔去。
清冷的雨滴细密地落在她单薄的娇躯上,冷意逼人,肚子里的孩子也被那道掌力惊动,不满地踢动起来,腹中闷胀作疼,胸口更是痛得火烧一样,乱雪难受只想倒在地下,可她却强撑着往宁王府的方向蹒跚艰难地走着,只有那里,才是她最依赖的地方。
不知道走出了多远,却一直没有走到那个地方,她终究是个柔弱的女孩子,跌跌撞撞地走到一座冷落角落里的小屋外,只来得及推开门就无力地倒在了里面,失去意识之前,隐约看到那似乎是座城隍庙。
这世上有很多事,人们往往在经历过漫长的离奇曲折之后,才会蓦然记起,一切的开始竟是那么简单却不经意。
那座平凡而简陋的城隍庙,就那样无声无息地在雨中静默着。即使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何况是这个清冷的雨夜?
四周很静,静得连雨声都变得虚幻飘渺了。两扇被乱雪推开的陈旧木门后,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昏暗里,那么让人不经意,那么简单…
(二)那时初见
天空阴云如墨,蒙蒙细雨不知什么时候下成了倾盆大雨。
这个季节本不该有这么大的雨的。
一个清瘦的少年在雨中踽踽独行,冠带束发,青衫磊落。身量挺拔,身影却说不出的落寞。他身后背着一把剑,那是一把古剑,古铜色的剑鞘上已染上了斑驳的锈迹。它同那少年一样在雨中沉默着,像是被漫长的岁月磨去了全部的锋芒,让人忘记了它曾是一把让人闻风胆寒的剑。
滂沱的大雨湿透了少年的衣衫,雨滴沉甸甸地砸落在他的身上,顺着他的额头,眼角,脸颊,像夺眶的热泪一样汹涌落下。可那不是泪,很久很久以前,他就知道了,一个男人决不可以流泪的,哪怕他再痛苦,哪怕他去流血,都不能流泪。他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这是他一生这十九个年头中除武功之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他似乎已经做到了,因为那双坚毅的眼眸中的悲伤深得似已透入骨髓,流淌在全身的血液中,他却终究没有落泪,哪怕他心中早已泪雨滂沱。
江循早知道大哥江序独身在龙潭虎穴之中的,一年前他武功初成,就赶来应天府想要助他一臂之力,可江序却执意要让他先去江湖中闯荡历练。江循性子淡薄,因此这一年中虽然武功日益精进,却一直声名不显。三天前,他突然得到宁王府中的密讯,换日阁暗中聚集人手,似乎要有什么动作。江循当时正在淮南,他其实清楚江序的武功深浅,即使是换日阁凶名昭著的四大杀手中武功最高的离风也要逊大哥一筹,但心中却没来由的生出一丝不安来。他匆匆放下手头的事情,换马疾奔了两天两夜,这天半夜才冒雨赶到南京城。
可他万万没想到,等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万花楼,见到的居然是江序的尸体!霎那间江循如同身坠百丈冰窟,一颗心冷了个透彻,他只晚来了半个时辰,可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生悔痛!
江循在江序的尸身前站了很久,始终沉默不语,颤抖的身躯渐渐回复平静,但那道原本沉稳的目光中的锋芒却越来越难以掩饰。可他硬是忍住了只差一点就夺眶而出的热泪,差一点把牙齿咬碎,最终连那道锋利的目光都暗淡下去,他还是没有说一句话,深深向江序望了一眼,转身向外面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迅急的大雨披头盖脸地落下来,江循却恍若未觉,径直走入雨中,任凭大雨肆意洗刷着身体。“房间里经过了一场短暂的打斗,尸身上却没有任何外伤,血色乌青,这是身中剧毒之相,老鸨也说刺客是个少女,换日阁中只有一个女人精于用毒,难道是她?”心中默默想着,江循行走在夜雨空巷中的脚步仍是那么缓而坚毅,用只有自己听的到的声音轻轻道:“我会替你报仇,无论那人是谁,都要付出代价。”
远远的看的到暂时憩身的城隍庙了,江循的目光忽然沉了沉,那两扇原本关好的门是开着的,他脚步不停,不动声色地走了进去。小庙里的东西并不多,因此那个倒在地下的身影多少显得有些突兀。江循皱了皱眉头,随手点亮了灯烛,这才慢慢走了过去。那人无声无息地侧躺在地下,似乎已经昏迷了,身形纤弱玲珑,似乎是个女子。
武林中年青的一代,江序的武功已经算是卓尔不群了,便是当世成名已久的一流高手跟他过招也是有败无胜。但很少有人知道,江循十四岁之后,江序跟他交手输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赢过。江序四年前就开始出来闯荡江湖,数年不见,连江序都不知道江循的功夫到底有多高了。而他武功既高,这一年的江湖闯荡更让他见惯了世事险恶,因此对方虽然看上去没有危险,江循的左掌仍是暗中微微抬起,以防她突施暗算。
靠近以后,江循不由的怔了怔,虽然有些零乱的发丝遮住了眉眼,可仍然能看出那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女。她气息急促微弱,俏脸煞白,显然是受了很重的内伤,是真的昏迷不醒了。
江循神色一缓,这才发现这少女的肚子高高隆起,竟然还怀着身孕。他早看出她身有武功,不由的对她的来历十分好奇。
犹豫了一下,江循还是伸臂扶她坐起身子。少女伤的不轻,又挺着大肚子,如果不管她,只怕情况就不妙了。不管怎么说,先救下她,等她醒来后再问经过不迟。
少女娇躯软软倚靠着江循的手臂,浓密的青丝顺着脸颊缓缓滑落,江循有意无意地瞥了她的样子,就那么匆匆一瞥,他的目光就是一震,居然看得入了神。
江循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少女的容貌,不倾国倾城,不媚惑众生,只是感觉她很美,眉目温润,粉颊皓齿,纯净得像是没有沾染一丁点尘世的污浊,让人心里不由自主的想到那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
江循自由生长在黄沙漫天的大漠,又专心武功,涉足江湖以来虽然难免遇到形形色色得美貌女子,但对他来说却都如同过眼云烟,从不放在心上。他从未想到,这世上居然会有一个女子能让他舍不得移开目光。她神色疲惫憔悴,美眸紧闭,因为胸口的痛楚皱眉轻咬樱唇,竟然让他莫名其妙得心疼起来,一抹冷幽幽清淡淡的甜香更是从她柔软的身体上若有若无地飘过来,江循几乎感觉自己是在虚幻的梦境中了。
乱雪忽然下意识的痛吟了一声,娇躯挣开江循的手臂,却又抱着大肚子软倒在了他怀里,身子难受的颤抖起来。江循被她的异样惊动,终于回过神来,这才惊觉怀里的少女俏脸上冷汗津津,一股强横的内力在她体内横冲直撞,受惊的胎儿也不安的挣扎着,痛的她缩在他怀里没有意识地难过呻吟,温软的大肚子更是紧紧顶在他小腹难受地磨擦着。江循武功再高,终究也是个十九岁的少年,怀抱着一个娇弱动人的妙龄少女,她柔软的娇躯紧贴着他的身子,他居然也不禁是一阵面红心跳。他开始还有些手足无措,可怀里的少女内伤发作,捂着胸口吐出一口血,抱着肚子痛的浑身发抖,却又始终昏迷不醒,情况实在是有些不妙。
江循暗骂一声:君子坐怀不乱!深吸一口气,总算压下心里杂乱的念头,小心翼翼地扶正少女的身子,玄功在体内自然留转一个周天,缓缓伸出手掌抵在她背后,将一股温和的内力慢慢送了过去。
江循内力深厚,虽然只是缓缓送去,乱雪体内乱窜的仍是慢慢停滞下来。可当江循的内力与那道灼热刚劲的内力接触到一起,他的神色却猛然变了,霍地收回手掌,双目如电死死盯着那个柔弱娇怯的少女。
没人能比他更熟悉那道火热的掌力了,因为他自己的内力就是那样的,那分明就是江家的独门武功焚阳功!
他的目光随即落在少女隆起的肚子上,猛地想起,杀死江序的那个刺客还怀着身孕!一念及此,江循忽然伸出手在她腰间摸索,很快就找到一枚雕着黑日的玉佩,上面虬劲古朴地刻着一个“雪”字。换日阁排名第二的杀手乱雪,竟是这样一个清纯柔美、楚楚动人的少女。
江循悲怒交加,怒叱声中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掌拍向少女的额头。他这一掌使足了内力,手掌一扬,两人的衣襟已经被那骇人的掌风激得四散飞扬,这一掌若是击中了,别说是一个娇弱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尊石像也会打成粉末!
江循的掌心离乱雪的额头只有半寸,只要手掌微微一送,怀中的少女就会立刻香销玉殒,可他这一掌却停住了。
江循望着她近在咫尺的清纯得似乎轻轻碰触就会烟消云散的苍白俏脸,他原本沉稳的手掌居然开始漱漱颤抖。仇恨使他整个人陷入激怒,他还从未对谁有过这么重的杀意,可无论他怎么催动内力,颤抖的手掌不断抬起又落下,却就是没办法拍下这一掌去。他不可思议得发觉,自己竟然狠不下心去杀她!
有很多事,有很多人,明明知道是错的,人们却总是身不由己得去继续,去靠近,因为冥冥之中早有一份缘在等待着。无论是否察觉,每个人都在按照缘留下的痕迹交集着,没有任何道理,没有谁能挣脱。
就像直到很久以后,江循才知道,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对她下手,为什么她痛的皱眉轻吟,他竟然忍不住心疼。
因为在他瞧见她第一眼时,一切早已注定…
江循的手掌还是落了下去,却是重新按在了乱雪的背后。
“江循,你一定是疯了…”他颓然自嘲,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温和的内力慢慢送过去,神色却满是挣扎,复杂烦闷之极。沉了一沉,他忽然想道:“她终究只是个身不由己的杀手,始作俑者却是宁王!我去杀了宁王,才算给大哥报仇!”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借口,但眼中的烦乱却渐渐平静了下来,只剩下一抹若有若无的黯然。
焚阳真气至阳至刚,乱雪体质阴柔,江序最后这一掌更是将残余内力尽数拍出,这道掌力在她体内横冲直撞,她又大着肚子,用外力强行逼出势必会伤到孩子,这内伤着实棘手。可焚阳功本就是江家绝学,这道掌力对江循来说形同己出,他的内力还要强过江序,因此他淳厚的真气只在乱雪体内转了几个周天,便把那道霸道的掌力彻底化去。
如果江循不是江家后人,这时只怕就要大费踌躇了。但既然已经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接下来要做的就简单的多了。江循内力深厚,乱雪本身的保护胎儿的内力在他的引导下渐渐恢复到丹田,随着静脉渐渐温养自己的内伤。乱雪的脸色虽然依旧苍白,神情却平静了下来,双手自然而然地抱着鼓鼓的肚子,粉颊上渐渐有了一点血色。
江循收回内力,默默站起身来,没有再看那个盘坐在地的少女,也没有再做什么。他的衣服早已被内力烘干,但一股冷意却还是顺着衣襟不住透进来,他轻轻叹了口气,慢慢走到里面那张落满灰尘的供桌前,席地而坐,眼眸微阖,像是睡着了一样。
乱雪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她有些茫然得扶着肚子站起身来,忽然发现胸口的痛楚减轻了很多,体内催命一样的掌力也不见了踪影,这身内伤竟像是已好了大半。她愕然打量四周,才发现旁边燃着堆篝火,一个少年正无声无息地坐在那儿,架着铁锅在烧着什么。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剑眉虎目,目光沉静无波,脸色因为长年风吹日晒而呈现一种淡淡的古铜色,更使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多了几分沉稳坚毅。他身量高瘦,却并不瘦弱,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身体轮廓,年轻而有力。乱雪悄悄打量他片刻,他却始终不曾察觉一样的没有半点反应,乱雪有些惊讶的发觉,她居然瞧不出这少年武功的深浅,他身上几乎连任何学武之人该有的奇妙气势都没有。
“你醒了?”少年没有回头,忽然道。乱雪轻声道:“是你救了我?”江循微微点头,却还是不去看他,淡淡道:“算是吧。”乱雪看着他挺的笔直的冷淡背影,欲言又止,两人都没有再说话。江循默默望着那团跳动的火焰,面无表情,乱雪低头轻轻抚摸着隆起的肚子,神色温柔。四周忽然安静下来,只剩下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单调的重复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冷幽幽的声音突然传入小庙,打破了这微妙的沉默:“阿雪,你在这里吗?”这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显然说话的人内力修为深厚,虽然语音冷的出奇,但谁都听得出其中毫不掩饰的关切。
江循盘膝而坐,恍若未觉,乱雪却神色一喜,挺着大肚子快步推门出去,反手把庙门关好,挡住江循的身影,这才回答道:“风哥哥,我在这里。”
话音刚落,一个淡淡的影子就丛街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一身淡青色的长袍,面色苍白,目光森冷,一股犹如寒冬急风一样的冰冷气息围绕在他身边,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打个冷战,这分明是一股浓浓的杀气,一个手上沾染了无数鲜血的人才能磨炼出的杀气!
看到乱雪,离风冷漠的脸上终于有了几分暖意,轻声道:“阿雪,你还好吗?”乱雪点点头,问道:“风哥哥,你怎么来了?”离风微微一笑:“我今天凌晨到的,不放心你,就过来看看。”他说的轻描淡写,乱雪却知道离风三天前接到任务到杭州去杀一个江南武林故老,三天时间来回已经有些匆忙,何况还要完成任务?他一定是知道她要来刺杀江序,这才奋不顾身地冒险仓促去杀那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帮她。看着离风隐隐带着尘色的疲惫面孔,乱雪芳心就是一阵温暖柔软。无论何时,眼前这个在人前冷酷无情沉默寡言的男子,都在这样默不作声地悄悄护着她,她知道,他从来都把她的安危看的比他自己都重要。
“你受伤了?”离风忽然柔声道,这个素以“冷血无情”而让武林正邪两道闻风丧胆的换日阁第一杀手此刻的神色竟是那样温柔。乱雪却是美眸幽然,轻轻摇头道:“我没有大碍,江序已经死了。”离风点点头,注视着她还有些苍白的俏脸,忽然有些无奈地叹道:“王爷不该让你来的,你的身子…”
“风哥哥,你别怪他。”乱雪却忽然打断他,咬着唇轻柔而坚定地道,“王爷要做的事,咱们两个无论如何都要替他完成的。”离风默默望了她下意识地伸手抚摸着的浑圆肚子,目光微不可察地一黯,随即轻声道:“不错,咱们有什么资格责怪王爷呢。”神情甚是凝重。
沉了一沉,离风才继续道:“你一个人在这里疗伤么?”乱雪知道换日阁绝非善地,不愿让那个萍水相逢却救了自己的少年牵扯近来,这才看似随意地关门掩藏他的身影。见离风似乎并未注意到江循,她暗中松了口气,轻笑道:“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咱们这便回去吧,后天就是王爷祭天的日子了,咱们得仔细准备,莫要出了岔子。”离风点头道:“好,走吧。”说着扫了那座城隍庙一眼,没有什么异状,他人才转身向宁王府的方向走去。
乱雪望着离风的背影,心里隐隐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悄悄望了那两扇虚掩的庙门,却仍然是寂静无声,她这时不便跟那少年告别,也没有多想,扶着肚子快步跟上了离风的步伐。
小庙里,江循默然面对着柴火,乱雪和离风的对话声音很轻,他却听的清清楚楚。他浑身纹丝不动,眼睛也已经闭上,如果不是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几乎让人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乱雪下意识觉的哪里不对劲,其实是因为离风没有发现江循。离风武功为换日阁杀手之首,耳力自然十分灵敏,况且他自幼被严酷训练隐匿刺杀之道,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方才他站在庙外,虽然有门墙阻挡,但与江循的距离不过两丈远,这么近的范围,无论江循是否会武功,他的呼吸心跳之声也绝逃不过离风的耳朵!
可离风就是没有察觉到他,一点也没有。这种事情,离风成名后的这几年中只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可那人的武功之高,乱雪早已无法看透,这少年年纪还要比她稍小一些,武功最多也就能跟她比肩,又怎能避开离风的灵识?
许久以后,火上的铁锅中忽然传来水沸腾一样的声音。江循终于睁开眼睛,伸手提起锅盖,一股清爽醉人的酒香忽然飘然开来,那居然是一小锅醇厚的美酒。江循从旁边拿起一个模样古怪的瓷杯,探手舀了一杯热腾腾的烈酒,竟然仰头喝了下去。这杯酒煮到沸腾,温度何等之高?寻常人就是被溅到身上也要皮开肉绽,可他一口气喝了满满一杯,竟然连脸色都不曾红一红,这情形说来着实是古怪之极。只有武功深湛之人,才看的出这年纪轻轻的少年实是有一身匪夷所思的阳刚内功。
江循放下杯子,点头道:“南京城中竟然有这样好的酒,也算是难得了。”说着,伸手从背后把那把剑解下来,缓缓拔出剑身。那剑似是有很多年没有出鞘了,不但剑鞘上锈迹斑斑,剑身也满是暗锈,色泽黯淡,几乎如同一块废铁了。或许早已没有人记得,这把剑曾经同它的主人一样威震天下,为世人所敬仰。
剑名“激扬”,取自“激浊扬清”,乃是江家先祖宁远公的佩剑。宁远公是大明太祖皇帝麾下名将,少年时便已纵横江湖,罕逢敌手,中年投入朱元璋军中,随他扫灭群众,打下锦绣河山,立下了赫赫战功。无论是陈友谅、张士诚手下高手还是蒙元帐中异士,在宁远公手下均是铩羽而归,从无半点胜绩。更因他出手果决霸道,落败对手非死即伤,群雄对他又敬又畏,江宁远和他的激扬剑,在百余年前威名之盛,实已无人堪比。
大明立国之后,宁远公云游途中偶遇世外仙道点化,顿悟自己一生伤人无算,损伤天和,实已违背了习武之人感悟天道、诚敬天地的根本。宁远公隧归还太祖皇帝封赏,举家远赴大漠,终生再未返回中原。
沧海横流,倏忽百年,当年的英雄故事早已如同这把激扬剑,淹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更因江宁远传下遗训,江家后人不得轻易踏入中原,曾威震天下的江家就这样销声匿迹,渐渐消失在了世人的记忆之中。
江循再次舀起一杯烈酒,神色庄重地缓缓倾倒在剑身上,那道灼热清澈的酒水在剑身淌出存余竟已渐渐消失。江循毫不迟疑,再次舀出一杯倒在剑上。他一杯一杯的舀出,剑身的酒迹也一寸一寸的扩大,倒像是那剑在饱饮美酒一样。
随着烈酒的浸透,剑身的锈迹竟是渐渐消退,仿佛一轮冷月在乌云后渐渐透出清凉的寒光。终于,待那铁锅中最后一杯酒倒尽,激扬剑最后一道暗锈也被洗去,一抹淡淡的剑光随着江循的手指虚幻缥缈地散到四周,小庙里仿佛一下子冷了下来。
这把剑像是在那瞬间有了生命,虽然随即光芒便已消失,但剑身却皎然如月,清冷如雪。
江循怔怔瞧着手中的激扬剑,太师父将它传给大哥,大哥又将它交给他,如今剑已出鞘,可识剑之人除了他竟然都已不在人世,这是怎样一种黯然神伤?当初江序半是郑重半是期望得把剑交给他的情形似乎就在眼前,可他伸出手指,却只能摩娑到冰凉的剑身,再也不是那个潇洒风流却其实满腔热血的高大身影了…
江循抚摸着剑刃,声音轻的不知是对剑还是对人说的:“这酒,就当是咱们一起喝的,明天咱们一起去做个了结,我便带你回家…”
窗外有抹初阳露出云端,照在雨后薄雾氤氲的长街上,清淡,微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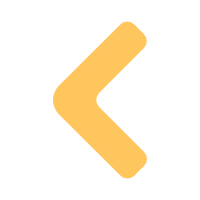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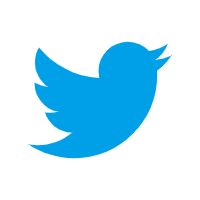




Comments NOTHING